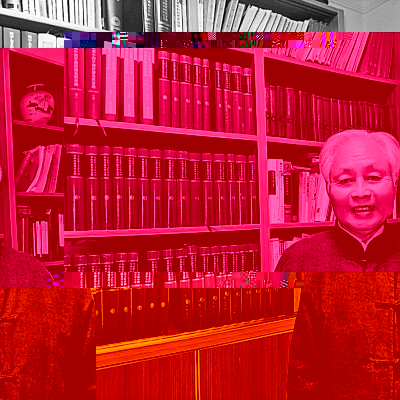
學人小傳
田子渝,1946年生于重慶。中共黨史專家,永利教授,曾任北京大學《馬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長期從事中共黨史人物、湖北地方黨史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李漢俊》《武漢五四運動史》《湖北新民主革命史(解放戰争時期卷)》《走進史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史(1918—1922)》;主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著作叢編(1920—1927)》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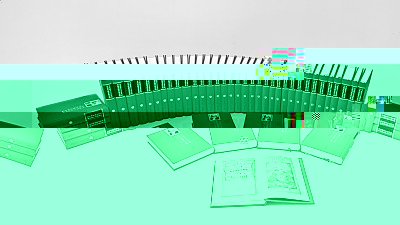
田子渝主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著作叢編(1920-1927)》。本版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2023年9月的一天,田子渝教授在工作微信群中轉發了群内一位青年學者新近發表的一篇論文,留言道:“請各位尤其是年輕的博士們學習此文。在浩瀚的史料裡做黨史研究,不是一日之功。有些人喜歡跟風,喜歡短平快,喜歡拉關系,那是做不出學問來的。這篇論文給我們的啟示就是要充分利用豐富的原始資料,從小問題入手做大文章。加油!”這個工作群中的30多位學者,來自全國各地10餘所高校和科研單位,因為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史研究的共同興趣,會聚到田子渝教授的團隊之中。
盡管近年來田子渝教授身體狀況不佳,但是他的大腦一直在高速運轉,一直在思考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典籍的收集、整理與研究工作。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是他“晚年最關心的事情”。實際上,田子渝關注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研究,可以追溯到40多年前。
從研究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起步
田子渝的學術生涯是從研究恽代英、李漢俊、董必武等中共早期領導人啟航的。
田子渝出生于一個紅色家庭,父母都是20世紀30年代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父親曾在董必武身邊工作多年。受家庭熏陶,田子渝從小就對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的生平與思想充滿興趣。上小學時,他就開始思索,為什麼董必武、李大钊、恽代英等人作為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願意放棄原本優越的生活條件而投身革命?他們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到底是基于怎樣的理想、信念與追求?
1979年,時值五四運動60周年,田子渝受湖北少年兒童出版社邀請,撰寫一本講述恽代英故事的學生讀物。恽代英是中國最早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之一,被周恩來稱為“中國青年熱愛的領袖”,1931年犧牲時年僅36歲。為了寫好這本書,田子渝四處走訪恽代英的研究者。在武漢,他訪問并結識了家父李良明(時為華中師範學院青年教師),從此結為莫逆之交;在北京,他拜訪了恽代英日記的主要整理者張羽(中國青年出版社資深編輯),獲得了不少第一手資料。田子渝還鼓足勇氣給鄧穎超等曾與恽代英共事過的革命前輩寫信。在鄧穎超的推薦和鼓勵下,田子渝采訪了恽代英的夫人沈葆英,連續幾天聽她口述恽代英的生前往事,為創作增添了大量鮮活素材。
一年後,田子渝完成了近7萬字的《留得豪情作楚囚——恽代英的故事》,署名“鐵流”。這是新中國第一本介紹恽代英事迹的少兒通俗讀物,文字淺顯易懂,内容生動感人,甫一出版就廣受歡迎。筆者當年就是該書的第一批小讀者,至今仍記得當時小學同班同學們争相閱讀該書并撰寫讀後感的情景。從此,恽代英等中共黨史人物成為田子渝學術研究的方向之一。他先後發表有關恽代英生平與思想的論文10餘篇,并于1984年與任武雄、李良明合作編撰出版了國内第一部恽代英傳記。
在研究恽代英的過程中,田子渝接觸到關于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和啟蒙者之一、中共一大代表李漢俊的一些資料。建黨三年後,李漢俊就因自動脫黨而被黨除名,加上犧牲得太早(1927年遇害),長期以來受到一些不實指責,其曆史功勳也一直被湮沒在曆史的塵埃中。1980年,田子渝在整理父親田海燕當年為撰寫《董必武傳》而收集的資料時,發現董老在自述中尊稱李漢俊是他的“馬克思主義老師”。這令田子渝大感驚訝,他敏銳地認識到有必要對李漢俊作出符合曆史真相的客觀評價。于是他潛心埋首,梳理了大量關于李漢俊的原始文獻資料,并與中共一大紀念館的陳紹康等人合作,在《武漢師範學院學報》1982年第6期發表了1萬多字的《李漢俊傳略》。這是改革開放以後學術期刊上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比較全面地介紹李漢俊生平事迹的文章,恢複了李漢俊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者、中共主要創始人之一的曆史本來面貌。随後該傳略由作者擴充至3萬多字,被著名中共黨史專家胡華主編的《中共黨史人物傳》第11卷收錄,于1983年出版。胡華教授贊揚田子渝:“以前我們對李漢俊了解甚少,你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
在胡華、彭明、鄭惠、張靜如等前輩專家的鼓勵下,田子渝遍訪李漢俊的學生、親屬和後人,堅持不懈地收集、整理和研究李漢俊遺著,挖掘出李漢俊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文章100餘篇,不僅發表了多篇相關學術論文,而且獨撰了近20萬字的專著《李漢俊》,作為“中共一大代表叢書”之一于1997年出版。經過田子渝和同行們的共同努力,李漢俊的曆史功績終于得到承認,曆史地位得以恢複。2002年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産黨曆史(第一卷)》寫道:“在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李達、鄧中夏、蔡和森、楊匏安、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趙世炎、陳潭秋、何叔衡、俞秀松、向警予、何孟雄、李漢俊、張太雷、王盡美、鄧恩銘、張聞天、羅亦農等一大批先進分子,先後走上無産階級革命道路,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在維經斯基等人的幫助下,陳獨秀以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為基礎,加快了建黨工作的步伐。1920年6月,他同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等人開會商議,決定成立共産黨組織,并初步定名為社會共産黨,還起草了黨的綱領。”
鑽研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史
通過對恽代英、李漢俊、董必武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研究,田子渝收集和整理的有關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史的第一手資料日趨豐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恢宏畫卷在他的腦海中越來越明晰、立體。于是他開始投入大部分精力,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史,其代表性成果就是2012年由學習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史(1918-1922)》(以下簡稱《傳播史》)。此書近60萬字,被學術界譽為該研究領域的“扛鼎之作”。
《傳播史》之所以将時間上限定為1918年,是因為田子渝認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自覺傳播的發端是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之所以将時間下限設在1922年,是因為同年中共二大制定的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綱領證明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革命實踐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标志着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實現了曆史性跨越。在這部書中,田子渝非常注重史料的梳理與考據,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過程中所形成和積累的曆史文獻進行了空前廣泛的檢索和整理,挖掘出不少以往學術界關注不夠、利用較少的史料。他不僅充分運用《新青年》《每周評論》《星期評論》《民國日報(副刊)》《晨報(副刊)》等早期報刊和《階級争鬥》《唯物史觀解說》《工錢勞動與資本》《社會主義讨論集》等早期著作,作為立論的史料基礎,還全面利用李大钊、陳獨秀、李達、瞿秋白、蔡和森等一大批早期傳播者的全集、文集,以及“共産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運動檔案資料叢書”等專題文獻資料,引證的史料具有原始性、廣泛性、權威性,極大地增強了論點的說服力。
在人物評價上,田子渝充分肯定李大钊、陳獨秀、恽代英、蔡和森等人的重大貢獻;同時也對李漢俊、施存統、張申府、劉仁靜等人的曆史功績給予實事求是的評議。這種客觀的寫作态度與求真的治學精神使這部書多維度、全景式再現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斑斓輝煌、群星燦爛”的曆史,成為一部“史由證來、證史一緻;論從史出、史論結合”的作品。
尤其難得的是,田子渝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從國内外搜集了近300幅珍貴照片刊于書中,其中不少照片是首次公布,進一步增加了學術信息量和曆史厚重感。有學者評價:“該書從縱向梳理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的曆史脈絡,從橫向探讨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涉及的黨派、群體、機構、媒介、渠道、思潮、傳播内容和國際因素等,用大量不可撼動的史實證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是近代中國救亡運動的必然結果,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人民正确的選擇。”
優秀成果的背後,是田子渝艱辛的付出。這部書從2004年動筆到2011年定稿,整整用了7年時間。田子渝為撰寫此書度過了無數個不眠之夜,厚厚的書稿已記不清曾反複修改過多少遍。筆者作為與其熟識的晚輩,最直觀的感受就是,在該課題立項之初,當時已近花甲之年的田先生氣宇軒昂,滿頭青絲,看上去似乎隻有40多歲的樣子,人人都誇他顯年輕;可是待到7年後成果出版時,蓦然間發現他已經是華發叢生,舉手投足雖然依舊風度翩翩,但是常常略顯疲态,一望即知其為年近古稀之人。田先生的摯友、家父李良明教授曾對筆者感歎道:“老田視學術如生命。為了寫好這本書,他真的是透支了身體啊!”
彙編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文本
《傳播史》給田子渝帶來了崇高的學術聲譽。2014年,68歲的田子渝辦理了退休手續。有人勸他,既已功成名遂,理應好好休息、頤養天年。可是,田子渝老骥伏枥,志在千裡,繼續在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研究這片沃土上辛勤耕耘,隻盼在有生之年實現自己的學術夢想——對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的著作文本進行系統搜集、整理和研究。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精神洗禮,凡欲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共創建史,就得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著作文本進行詳細梳理、考察和解析。然而截至田子渝退休時,這個方向的工作可謂鮮人問津,因為這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推出高質量成果既難又慢。田子渝秉持探尋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源頭活水的初心,不計得失,奔走于海内外多家學術單位和文博機構,嘔心瀝血地檢索、整理各種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的著作文本,一心要開辟出一片新的學術天地。
2017年,田子渝作為首席專家申報的教育部社科研究重大項目“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史料收集、整理與研究”獲批立項。年逾古稀的田子渝召集來自永利、北京大學、華中師範大學、中南民族大學、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嘉興學院等單位的學者,組成一支老中青結合、跨省、跨校、跨學科的研究團隊,開始編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著作叢編(1920-1927)》(以下簡稱《叢編》)。他從自己曆年收集的250多種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著作文本中,精選出具有重要曆史地位、廣泛傳播影響和獨特思想價值的151種珍稀版本,組織團隊成員分别對其進行細緻的整理、校訂、注釋和說明,彙編成45卷叢書,開創了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大型史料編纂的先河。
這項基礎性文化工程的挑戰性超乎想象。所有的文本都是将近一個世紀前的作品,文言文、白話文混雜,甚至譯文語義不标準,許多人名、地名、術語與現今差别很大,光是馬克思的譯名就有“麥喀氏”“馬爾格士”“馬格斯”“馬克斯”等10餘種。對文本内容進行疏解、考證是《叢編》編撰過程中工作量最大,也是難度最高的部分,涉及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版本學等衆多學科的專業知識,稍不留意就會弄錯、出現硬傷。筆者忝為團隊成員之一,至今回想起大家在田先生的領導下精誠合作、協同攻關的往事,仍然心潮澎湃、百感交集。夜深人靜之際,包括田先生在内的不少團隊成員,往往還繼續在微信工作群内熱烈讨論某處“注釋”應該如何修改、某篇“說明”應當如何潤色。盡管當時感到有些疲倦,但是一想到年邁多病的首席專家尚且沒有休息,仍在堅持工作,我們就又充滿了力量。
為了做好文獻整理和考據,田子渝不顧自己患有嚴重的高血壓和心髒病,多次率團隊成員赴北京、上海、重慶、廣州、南京、澳門等地的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仔細查訪,窮幽探微,盡最大努力尋找中文首譯版本,并與外文原著進行認真比對,訂正翻譯失真之處,更改錯字、别字,同時對每種文本的創作背景、主要内容、社會影響、曆史地位等進行闡釋,以方便當代讀者理解。《叢編》共計2700餘萬字,其中對文本的“注釋”和“說明”就達310餘萬字,絕大多數中文譯文都對照了外文原著,一些釋文填補了馬克思主義傳播史研究領域的空白。
2021年10月,《叢編》首發式在武漢舉行。田子渝及全體團隊成員通過将近5年廢寝忘食的辛勤勞動,為中國共産黨百年華誕和新中國72歲生日獻上了一份厚禮。學術界對該項成果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叢編》搶救和保存了一批珍貴的文獻資料。
深挖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的“富礦”
《叢編》的出版遠非田子渝學術生涯的終點。在他眼中,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研究領域是一座“富礦”,仍然蘊藏着許多值得長期關注和深入探究的重要選題。《叢編》的問世為更好地研究這些選題創造了條件。
例如,長期以來,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早期傳播的研究十分有限。在已有的成果中,碎片化、同質化現象比較普遍,主要原因在于很多研究者并未充分掌握這方面的原始著作文本。《叢編》輯錄了集中反映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婦人與社會》《婦女之過去與将來》《社會主義的婦女觀》等9種原著的早期中譯本。《婦女與社會主義》是德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奧古斯特·倍倍爾基于唯物史觀論述婦女解放問題的經典著作,先後被翻譯成10餘種文字,在世界各國反響強烈。1927年沈端先(夏衍)以《婦人與社會》為名将該書譯成中文,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在1995年中央編譯出版社推出新的中譯本之前,沈譯本一直是《婦女與社會主義》唯一的中譯本。要深入探讨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的傳播及其中國化,不可能繞開《婦人與社會》這部關鍵性譯著。但是截至目前,關于該書在中國對婦女運動的影響以及在婦女解放過程中的作用鮮有研究。
又如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傳播,學者以往的研究多半集中在魯迅和“左聯”方面。其實早在20世紀20年代,馮雪峰、沈雁冰(茅盾)、李漢俊、楊明齋等人就先後翻譯、編寫了《新俄羅斯的無産階級文學》《革命的文學》《無産階級與文學》《藝術與民衆的精神》《俄國文學史略》《評中西文化觀》等重要著作,為傳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作出了傑出貢獻。其中馮雪峰以筆名“畫室”翻譯的《新俄羅斯的無産階級文學》是我國最早譯介俄國無産階級文學的專著,為國人了解蘇俄文學發揮了巨大作用。魯迅曾在北新書局圖書廣告中大力推薦此書。但對以上這些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重要著作,當前學界的研究依然不夠充分。
再如,有些人物在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中發揮了較大作用,可是由于各種複雜原因,他們幾乎被湮沒在曆史的長河中。像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首個中文本的譯者鄭次川、《馬克思經濟學說》的譯者陳溥賢、《近世經濟思想史論》的譯者李天培、《共産主義與智識階級》的作者田誠等,當代學者對他們知之甚少。以《共産主義與智識階級》為例,該書1921年6月在武漢發行,首次旗幟鮮明地宣布在中國“第一步要組織無産階級的先鋒隊,就是共産黨”,第二步就要使無産階級奪得政權,建立“勞農專政的國家”,從而為中國共産黨的誕生創造了非常有利的輿論氛圍。但是“田誠”究竟是何許人也?生平事迹有哪些?至今仍是個謎團。筆者發現學界猜測田誠可能是陳獨秀、李大钊或李漢俊的筆名,并就此向田先生請教,他表示目前的證據仍然十分有限,既無法證實亦無從證僞田誠是誰的筆名。顯然,對以上人物進行考證,查清他們的真實身份、生平事迹、思想軌迹等,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田子渝希望,他的研究團隊能充分利用《叢編》彙集的學術資源,争取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中取得新突破。而他本人的下一個目标是撰寫一部《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通史》。我們相信,這将是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史研究新的裡程碑。
(作者:李天華,系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中南民族大學分中心研究員)
學人論學
有人類社會,就有文化;有文化,就有文化交流。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從20世紀初葉開始,馬克思主義這個出自萊茵河—泰晤士河畔人類文明的結晶,因其獨步人類思想的高峰,切合中國救亡圖存和民族複興的迫切需要,而在中華大地得到了廣泛傳播。
這是中西文化交流中極其特殊與輝煌的曆史。特殊,是因為它的傳播不同凡響——在東方落腳,并具有強烈的時代使命感。縱觀中外文化交流史,像馬克思主義這樣與民族命運聯系得如此緊密,以至于形成曠日持久的共産主義運動的文化傳播,絕無僅有。輝煌,是因為它與中國本土文化重構,造成中國文化亘古未有的革命——形成了具有中國文化血脈的馬克思主義,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人類文化譜系中,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裡,它獨樹一幟。“中國化”不僅徹底改變了中國,而且改變了世界!
為什麼一個外來文化有如此大的神力呢?這不僅是馬克思主義本身所具有的科學性、世界性、實踐性、階級性使然,更重要的是,它适應了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挽救日益危亡國勢的需要。16世紀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學西漸,中華文化通過絲綢之路照亮了西方世界。但當工業文明興起,古老的中國閉關鎖國,統治者“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使封建王朝日益落後。落後就要挨打,1840年英帝國的炮艦轟開了國門,天朝帝國逐漸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中國在西方列強掀起的瓜分狂潮中危在旦夕。
有侵略,就有鬥争;有壓迫,就有反抗;要救國,就要有先進的理論引領。鴉片戰争以降,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尋求救亡圖存的思想武器以圖複興。西學東漸,他們開眼看世界,覺悟到封建專制文化不能救中國,遂告别數千年農耕文明,擁抱先進工業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是戰勝國,德國是戰敗國。德國所攫取的中國山東半島的權益理應歸還中國,但西方列強在巴黎和會上竟将其轉給日本,令中國人民對資本主義極度憤怒,轉向對社會主義無比憧憬。于是,五四運動成為以上兩種覺悟彙合的契機,從此,中國救亡運動打開新局。在這個偉大曆史轉折上,“西學東漸”發生了質的飛躍,馬克思主義從各種西學中脫穎而出,使我國近代政治思想發生前所未有的革命。
打開中共創建至大革命時期這些滿載着曆史厚重感的紅色文獻資料,耳畔響起了中國共産主義運動先驅者們振聾發聩的聲音:“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将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馬克思底共産主義,一定可以在中國實行的,不過如何才能實行,卻全靠我們底努力了!”“應用馬克思主義于中國國情的工作,斷不可一日或緩。”
今天,我們對“早期傳播”紅色典籍的搜集、整理與研究,就是溫故而知新。早期紅色典籍是中國共産黨的紅色基因和精神族譜,中國共産黨人以此為起點,開始了跨世紀的長征,經曆千難萬險,百折不撓,千錘百煉,不斷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建設與改革相結合,不斷賦予其新的時代内涵,率領中國人民取得一個又一個輝煌成就,勝利地步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摘編自田子渝主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著作叢編(1920—1927)〈序言〉》
原文鍊接: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23-10/09/nw.D110000gmrb_20231009_1-11.htm